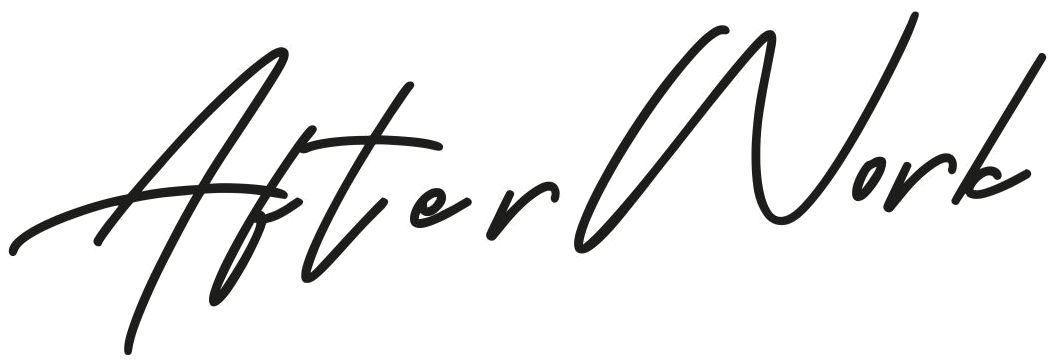准确找到定位,宛如新生

“Josh,80后,出生于雪兰莪锡米山新村(Sg Chua),后来移居柔佛峇株巴辖(Batu Pahat),毕业于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平面广告系,主修摄影,现为一个全职手作人,以经营“暮之森手工皂”(以下简称“暮之森”)为主。”
Q: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手工皂的?
最早接触是在第一次的台湾之旅,当时觉得手工皂的质朴原生感,有一种迷人的纯粹。初次使用后,可以清楚感受到皮肤毛孔通透的呼吸感,非常自在。
Q:后来是在什么契机之下,走上做皂这条路?
有次去市集买一张绝版的独立唱片,机缘巧合下,被朋友拉去参加一场基础打皂体验课,了解到它背后的关键词——环保。这个概念后来持续酝酿了一段时间。2016年,毅然决然走入另一个全新的场域去冒险。
Q:最后决定创业的那股劲儿源自哪里?
“创业”这个词在当初刚踏入社会时遥不可及。没日没夜地在设计及摄影的工作场景间来回切换了一段时间后,身心俱疲于机械式的操作,加上脑里有一头被围困的想象之兽(笑),觉得还不如正视内心的召唤——换一种更能自主掌握,更具创造力的工作形式,重新出发。
Q:为什么会给品牌取名“暮之森”,创作初衷是什么?
暮之森天然冷制皂,取大自然的恩赐(天然植物),造天然草本之日用,秉持“取之自然,用之自然”的原则,无论是对肌肤或大地,皆无毒无害。
我一直觉得充满生机,孕育许多不同生命的森林,是让人神往的梦幻之地。暮色将晚的森林,短暂而幽微的梦幻时刻,万物放缓脚步,静待夜幕降临。当时期许自己的手工皂可以让使用者在漫长的劳累后,短暂的梳洗过程中,深刻感受卸下疲惫的安逸、舒心的片刻。
Q:当初是先学会手艺,才发想品牌、研发产品的吗?
先苦练冷制手工皂,等到确认可以慢慢把作品分享出去时,才偶然闪现品牌的名字。当时受到许多日本、法国、希腊如安哲洛普的电影,以及现代诗的影响。
Q:暮之森的包装设计一直相当吸睛,是经过什么考量吗?
草创期着重于单纯的美好或“酷”,也非常幸运得到技术高超的画家——Cristjen Lai的眷顾,合作了一系列引起一些讨论声的作品。后来,决定发展出自己的插画系列,将重点放在人文或环境关怀的各种议题上,让作品的表达更有厚度和情感,让品牌核心更饱满鲜明。希望透过结合不同议题的插画,鼓励人们多关怀身边的人事物,多思考土地与万物之间的关系。
Q:如何让更多人认识“暮之森”,还是一直都是佛系经营?
在不少手作朋友眼中,确实有点佛系(笑),但我自己的理解是——一旦作品做好了,自然会有更多被看见的可能性,所以才会更专注在把作品做好这件事上。
Q:2022年7月,“暮之森”被遴选为首波长期入驻茑屋书店的手作品牌之一,可以说说心得吗?
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宝贵经验。只记得在非常短暂的喜悦后,接踵而来的是接连的高压和紧张,那时手头上还有三个案子在同步进行(呐喊)。要让如影随形的产品陈列在架上,是个对“自我表达”很重要的进阶过程。茑屋负责人一直给予充足且自由的表达空间,可以遇到如此优秀且尊重创作人的平台是有幸的,对于愿意提携非典型创作人的伯乐们,心存感激。
Q:品牌经营了七年,有没有遇过想放弃的时候?
起步那段日子是比较容易产生挫败感的阶段。除了要懂得精准把握做皂手艺,还要面对现实层面的问题,如要通过什么有效管道让群众看见、实际的生计等等。意志稍不坚定,热情就会在一波波的困难或不被理解下遭到侵蚀,极速消退。可当品牌轮廓渐渐被雕琢出来,就会宛如新生,持续茁壮。
Q:这一路走来,最深的体悟是什么?
待在手作圈子越久,就会看见一些重复性的“怪象”。近来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文创市集开始“被泛滥”的情景,不少单位标榜文创,实际上也许只有20%或更少的内容属原创手作。这些主办方会在名利双收后拍拍屁股闪人,长此以往,真正的文创市集会逐渐被污名化。
此外,有些商业单位会混进文创市集,用量产的产品以手作之名鱼目混珠,在盈利上尝尽甜头。这样的行为不但打压了珍稀的手作人,同时模糊了普罗大众对手作的认知,导致部分还未有机会成长的新晋手作人,热忱消磨殆尽,草创期就搁浅在沙滩上。看尽诸如此类的怪象,自己的追求和想法愈发坚定——寻找合适的平台(市集、合作对象等),无所畏惧地找到自己的“声音”,往往是这些独有的光彩,让品牌被看见。
Q:你觉得“暮之森”未来的走向是什么?
因为所有事皆由我一人主理,在贯穿各种创作风格时,可以跟自己的想法更紧密贴合、挂钩。在作品的层次和细节上,可以有施展美学以外,更值得玩味的空间。让作品朝“有趣有意思”“可持续衍生”“更自由地表达”等目标继续迈进。